唱片中的里赫特 | 成熟期的传奇: 里赫特 ——为音乐服务的诠释者
原作者: Klaus Bennert
翻译: 高阳之
简介:译者前言 1993-1994年,原荷兰PHILIPS唱片公司把Sviatoslav Richter(即:里赫特,俄国钢琴家)在该公司的录音整理发行,共11套双张CD,主要是里赫特晚年的录音。 PHILIPS公司被DECCA公司兼并后,DECCA又在2007年重 ...
译者前言
1993-1994年,原荷兰PHILIPS唱片公司把Sviatoslav Richter(即:里赫特,俄国钢琴家)在该公司的录音整理发行,共11套双张CD,主要是里赫特晚年的录音。 PHILIPS公司被DECCA公司兼并后,DECCA又在2007年重版了这套专辑,换上了DECCA商标。 我陆续买了10套,只缺第四集。 每套CD的说明书中,除里赫特的简介外,均有PHILIPS公司请音乐评论家或唱片业界人士撰写的评论文章,而且每套中的文章各不相同。文章作者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对里赫特的经历、性格、艺术成就和演绎风格等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给出丰富多彩的描述;作者并不都是毫无保留的里赫特拥趸,有些还对里赫特有时出现的技术问题颇有微辞;但是他们几乎都一致认为,里赫特不只是一位钢琴家,而且还是超越了钢琴演奏本身的一种艺术追求和文化现象。 对于只闻里赫特之名而没怎么听过里赫特琴声的人(我怀疑这是大多数),这些文章也许能够鼓励大家尝试一下“耳听为实”; 对于已经像我的一些乐友一样“陷入里赫特不可自拔”的人来说,这些文章也有可能为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揭示一些可以言表的依据。因此我不揣冒昧,在2021年疫情期间,斗胆开始把我收藏的这10套CD的说明书中介绍里赫特的文章译成中文,与我朋友圈中的同好者分享。这些文章陆续分享后,得到热心乐友的支持,还有乐友特意把我一直没买到的第四集的说明书发送给我,让我得以把全部11套CD说明书都翻译出来。 作为后记,我又把法国电影制片人Bruno Monsaingeon的《里赫特对话录》(Sviatoslav Richter: Notebooks and Conversations)一书的开始部分译成中文,便于乐友们对照参考。 希望有更多的乐友喜欢。
上个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居然实际上从未有过以努力取悦公众为目的的惯常职业生涯,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事情! 即使在青年时代,里赫特也没有走从众星捧月的神童,到在各种著名比赛中获奖这条通常的道路。在其他钢琴家早就在国际音乐舞台大放异彩的年纪,里赫特还在敖德萨 (Odessa) 歌剧院当排练指挥 (répétiteur):当他完成在莫斯科著名的钢琴教师涅高兹 (Heinrich Neuhaus) 门下的学习时,已经快30岁了。
里赫特气势磅礴的演奏在那个年代所向无敌,但他的演奏却从不以制造表面效果为目的,也从不肤浅。 在那个年代,他的艺术特点就是卓越的知性掌控,他的演绎来源于对音乐的极端复杂性和有机统一性的认识。当时涅高兹形容他对里赫特演绎风格的感觉时所采用的形象化语言可以原封不动地用于里赫特的晚年;涅高兹说,当里赫特演奏时,整个作品的呈现“就像一片大地,而他从高空以不可思议的敏锐目光扫视这片大地,既对整体一览无余又没有遗漏任何细节”。
曾经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壁垒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欧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听到有关里赫特的热情洋溢的报道,却无法见到里赫特本人。 里赫特变成了一头神话中的钢琴怪兽,一位来自传奇国度的谜一般的终极演奏家。 因此当他最终被允许离开苏联,首先到芬兰、然后又到美国演出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着期望值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这位敏感、内向的艺术家有时备受自我怀疑的折磨; 他感到自己被迫扮演最不适合的角色——一位震古烁今的超级巨星。
只有了解里赫特的人生背景,才能够理解他偏离正规职业生涯的最“出格” 举动——他对一切细节都事先计划好的商业音乐演出越来越多的抗拒。 他在一生中第二次停止向他此时已遍布全球的仰慕者们事先预告自己的档期——他又成为了一位活着的传奇。 顺便说一句,此事与老年人的悠闲自在毫无关系:1986年里赫特已经是71岁高龄,却举行了150多场音乐会; 但这些音乐会实际上已经不包括在事先计算好的长期日程中,而经常是由于里赫特发自内心地希望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演奏。 里赫特晚年似乎更喜爱法国谷仓、巴伐利亚修道院图书馆和意大利巴洛克剧院的氛围; 如果他真的出现在某个著名音乐厅的众多听众面前,大家倒会认为是一次特殊事件了。
这样一位表演者有时会让他的拥趸们很为难: 里赫特有时只提前几天才决定自己在何时何处演出,并且理所当然地指望他的听众能有办法搞清时间和地点。当然,实际上这就意味着里赫特的出场越来越成为只有那些能够理解这位大师古怪个性的人知晓的内部消息了。 对于广大音乐听众来说,幸好里赫特允许对他的音乐会进行现场录音,使那些一直无缘参加他的演奏会的人也可以体验他的琴艺带来的震撼。
不得不承认,即使最好的现场录音也难以传达晚年的里赫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几乎带有宗教意味的气息。那种对常规技巧性装饰的拒绝,在他的演奏会上并不明显; 里赫特坐在钢琴前面开始演奏,整个大厅一片黑暗,只有钢琴被一盏昏暗的台灯照亮,听众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音乐上而不是里赫特身上。 然而这也意味着,完全依赖于听觉的录音,又一次最终达到了里赫特完全专注于音乐的目的。
这些录音中收录的阿姆斯特丹和路德维希堡 (Ludwigsburg) 音乐会的曲目,似乎正是为了证明技巧应该以何种方式服务于音乐。的确,这些贝多芬曲目中也包括f小调“热情” (Appassionata)奏鸣曲,它的地狱一般的狂暴在里赫特较早的演绎中却达到了欣喜若狂的高度。 里赫特晚年演奏此曲时不像年轻时那样如醉如痴、毫无拘束,而是更具结构感、更加镇定自若,也更多一些客观性。 绝对价值变得比技巧更为重要,小品与大型作品一样得到重视。 阿姆斯特丹音乐会的曲目反映了典型的里赫特音乐品味:“热情”奏鸣曲, 加上两首“简单”的奏鸣曲(作品第49号), 和经常被低估的F大调奏鸣曲(作品第54号)。 在里赫特的思想中,似乎根本没有某些音乐属于“轻量级”的意识:他仔细研究小品,发掘它们未被认识到的伟大之处。 而路德维希堡音乐会的曲目——3首晚期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9-111号),则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领域:技巧变得抽象,变成了音乐内在特质的一种有说服力的展示。里赫特在演奏这些贝多芬曲目时的方法,体现了他晚年愈发趋于内向的轨迹:从以前的无与伦比的技巧大师,变成了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为音乐服务的诠释者。
浏览 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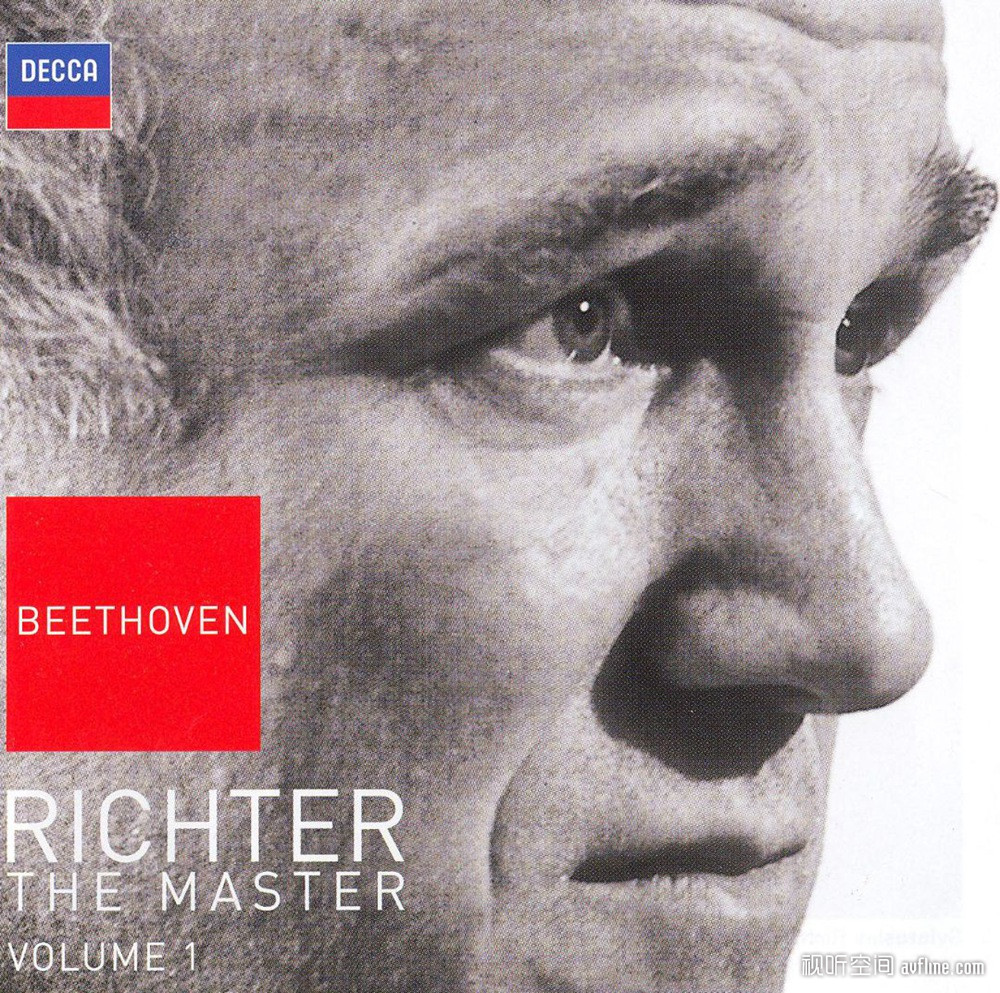





 新浪
新浪 淘宝
淘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