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中的里赫特 | 钢琴前的孤独者:Sviatoslav Richter 的键盘独白
原作者: Karl Schumann
翻译: 高阳之
简介:译者前言 1993-1994年,原荷兰PHILIPS唱片公司把Sviatoslav Richter(即:里赫特,俄国钢琴家)在该公司的录音整理发行,共11套双张CD,主要是里赫特晚年的录音。 PHILIPS公司被DECCA公司兼并后,DECCA又在2007年重 ...
译者前言
1993-1994年,原荷兰PHILIPS唱片公司把Sviatoslav Richter(即:里赫特,俄国钢琴家)在该公司的录音整理发行,共11套双张CD,主要是里赫特晚年的录音。 PHILIPS公司被DECCA公司兼并后,DECCA又在2007年重版了这套专辑,换上了DECCA商标。 我陆续买了10套,只缺第四集。 每套CD的说明书中,除里赫特的简介外,均有PHILIPS公司请音乐评论家或唱片业界人士撰写的评论文章,而且每套中的文章各不相同。文章作者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对里赫特的经历、性格、艺术成就和演绎风格等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给出丰富多彩的描述;作者并不都是毫无保留的里赫特拥趸,有些还对里赫特有时出现的技术问题颇有微辞;但是他们几乎都一致认为,里赫特不只是一位钢琴家,而且还是超越了钢琴演奏本身的一种艺术追求和文化现象。 对于只闻里赫特之名而没怎么听过里赫特琴声的人(我怀疑这是大多数),这些文章也许能够鼓励大家尝试一下“耳听为实”; 对于已经像我的一些乐友一样“陷入里赫特不可自拔”的人来说,这些文章也有可能为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揭示一些可以言表的依据。因此我不揣冒昧,在2021年疫情期间,斗胆开始把我收藏的这10套CD的说明书中介绍里赫特的文章译成中文,与我朋友圈中的同好者分享。这些文章陆续分享后,得到热心乐友的支持,还有乐友特意把我一直没买到的第四集的说明书发送给我,让我得以把全部11套CD说明书都翻译出来。 作为后记,我又把法国电影制片人Bruno Monsaingeon的《里赫特对话录》(Sviatoslav Richter: Notebooks and Conversations)一书的开始部分译成中文,便于乐友们对照参考。 希望有更多的乐友喜欢。
我听过里赫特几次,但不幸的是从来没有跟他交谈过。 一次交谈也许会证实我从他的音乐会得到的印象:一个孤独的人,从内到外都忍受着命运的煎熬,承担着责任和内心紧张的重压。 在今天的世界上,孤独就是艺术家的宿命。 《冬之旅》(Winterreise) 中那位流浪的悲剧人物转移到钢琴上——这就是里赫特给我留下的印象。 他似乎被舒伯特这部组歌中的寒霜和黑夜的形象所包围。 里赫特与许莱尔 (Peter Schreier) 合作留下了这部组歌的动人的录音:它就像是孤独的24个阶段,是里赫特在键盘上的自画像。
里赫特身上散发着压抑感。 听他的演奏,人们既不会欢欣鼓舞,也不会“升华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既不会感到惊讶,也不会感到孩子般的喜悦:人们只会想象自己面对着音乐的幽暗魔力。 据说舒伯特曾说他不知道有快乐的音乐; 里赫特肯定不知道有这种音乐。 不管他弹的是一首兰德勒舞曲(Ländler),还是一首活泼的练习曲(étude),支撑曲子的总是低沉忧郁的持续音 (pedal point)。 里赫特既不拐弯抹角,也不会变魔术; 既不世故,也不油滑——他直接就宣布紧急状态了。 他的技术令人目瞪口呆,但是人们并不太会意识到这种技术,因为他的技术完全是一种从属性的表达手段,几乎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里赫特弹最艰深的作品和弹最简单的作品一样,都是通过一种毫不松懈的表现力来掌控它。
有两场里赫特的独奏会,我无法忘记也不想忘记:1964年萨尔茨堡音乐节期间(当时这座城市还没有被火热的的音乐旅游行业所影响)在莫扎特厅(Mozarteum) 的舒伯特奏鸣曲,以及1975年在年轻的奥列格·卡甘 (Oleg Kagan) 首演音乐会上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 在萨尔茨堡音乐会上,当时50岁的里赫特演奏了我最喜爱的舒伯特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降B大调)。 萨尔茨堡通情达理地没有把里赫特安排在巨大的节日大厅 (Festspielhaus),而是让他在比较私密的、老派得很舒服的莫扎特厅举行演出; 在那里,舒伯特和里赫特这两个孤独的人的钢琴独白,不用担心会沦为旅游景点和娱乐活动。里赫特的形象令我震惊:忧郁、神经质、疲惫、苍白、饱经风霜。他几乎像超人一样的头颅低垂着,走向钢琴的样子活像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走向刑场。 破旧的晚礼服稍许有些小,他穿在身上似乎感觉不适。 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承受外部和内部双重压力的人,更像一个犯人而不是明星。他的演奏没有任何华丽的炫技; 当然那首降B大调奏鸣曲本来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技术难题。 里赫特完全忽略音乐厅里听众的咳嗽声,在钢琴上弹奏了四个乐章的独白。 那是一种志趣相投的灵魂的倾诉,充满痛苦和孤独。 对于里赫特来说,不严格按照舒伯特的指示全部重复演奏第一乐章那奇长无比的呈示部,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舒伯特这最后一首奏鸣曲中,“极强” (fortissimo) 力度是十分罕见的; 里赫特克制着自己,避免弹出任何轰鸣的声音,把他本可以不时露出的利爪隐藏起来。 一位好似饱受欺凌的内向的人,一位音乐独白者,却被称为明星,这让他沮丧不已。 而且这个人是生活在鞭子的威胁下的:我不知道苏联政权对里赫特的压制达到何种程度,但是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被利用、被榨取的人,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发笑的事情。 极少数情况下,我在里赫特脸上看到了抑郁症患者那种苦笑; 里赫特肯定有抑郁症。 无法判断他的抑郁是因为天才还是因为政治形势;也许二者都有吧。
舒伯特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简直就是通常音乐会曲目的反面,而里赫特的弹法正是如此:毫不做作,就像是弹一首触键和弱奏的练习曲,没有任何华丽的炫技,也没有感伤情绪。谐谑曲乐章一带而过,他的手指似乎都没怎么接触琴键。 第一乐章质朴无华,速度按照舒伯特的标记:十分中庸 (molto moderato)。低音部咄咄逼人的颤音作为标记在后来再次出现,暗示着在表面明亮的降B大调之下隐伏的阴影。每个三连音都表达得清晰如画。呈示部的结尾化作一片虚无,恰如一首带有维也纳风味的终曲 (Abgesang)。
俄罗斯小提琴家奥列格·卡甘(Oleg Kagan, 1946-1990)可以说是从旁门走进中欧各国的音乐厅的。里赫特毫不吝惜地用他自己的名声为卡甘的一系列贝多芬演奏会进行宣传。 公众对于奥列格·卡甘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他们以为卡甘是又一位快速升起又将很快被遗忘的音乐比赛获奖者,他们总是让音乐学者欣喜但让听众感到无聊。 进入音乐厅的两个人形成奇怪的对照:里赫特头发灰白,脸上布满繁重的专业生涯刻上的皱纹;而比里赫特年轻31岁的卡甘看上去就像一位俄罗斯的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英雄——译者注】,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稍许有些拘谨。 一般说来贝多芬的作品第12号中的3首小提琴奏鸣曲经常被当作暖场曲目,但在这里却上升为名副其实的富于表现力的双重奏鸣曲,由钢琴起主导作用。 里赫特的风格在本质上是抒情的,他坚持以希腊文的原意“痛苦”来表达“悲怆” (pathos),也就是理想主义的激情。 这种感情力量也可以在里赫特的“热情” (Appassionata)奏鸣曲录音,特别是他1960年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的录音中听到。那么在贝多芬作品演绎中的风格问题呢? 充沛的表现力本身就是理由。
显然钢琴的孤立让里赫特感到压抑,在听众面前孤单一人让他感到尴尬。 他在室内乐演奏中似乎更为放松:与鲍罗丁四重奏 (Borodin Quartet)演奏勃拉姆斯、与罗斯特洛波维奇 (Rostropovich) 演奏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还有弗朗克和德沃夏克的作品。 有志趣相投的人在场能够帮助他放松下来。
与其说他是一位钢琴家,不如说他是一位音乐家。 据说他本来想当指挥——不难想象里赫特指挥的舒曼和勃拉姆斯交响曲、巴赫的受难曲、柴可夫斯基管弦乐作品。 同样不难想象作为一名学者、甚至作为一位僧侣的里赫特。 他总是包裹在孤独之中,这是属于内向者的王国。
他是音乐界少见的晚熟者:在他开始出名的年纪,其他人都已经在全球巡回演出好几趟了。 但是这种晚熟也给了他优势:迟开的花开得更长久。除了几次早期的演出以外,里赫特成为一位巴赫演绎者用了很长时间。 他在巴赫身上花费了很多心力。 对于一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俄国成长起来的音乐家来说,巴赫是很不容易接触到的: 他被认为是一座巴洛克复调音乐的纪念碑,与俄罗斯感情丰富的气质和斯大林主义美学都不兼容。 后来,里赫特终于可以简单地宣布要开全巴赫曲目的演奏会; 他觉得那种提前好几个月宣布的节目单非常拘束,而且后来他的年纪和声望也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这样他就能全身心地投入音乐之中。 里赫特的巴赫可能会让历史纯粹主义者感到不安:这种巴赫在音色和精神上都是属于现代大钢琴的,是清晰而从容地表达出来的; 不是严格根据对位规则拼出来的抽象拼图,而是充满兴奋、敏感和高贵的音响、掩盖在严密的形式之下的富于表现力的音乐。 我认为里赫特的巴赫演绎是不可或缺的: 它们表现出了巴赫的伟大,他是一位在陈规俗套统治下的年代里,用热情洋溢的表现力填满那个年代密码式格律的伟大作曲家。
我特别钦佩里赫特的一种特质是他高尚的神经质,这使他不会不断地机械重复同一种弹法。他的每次演奏会上演奏方式都各不相同,因为他总是以全新的方式演绎一部作品。 里赫特的风格是无法复制、甚至无法模仿的。 也许,至少我希望,能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 不论演奏了多少次,里赫特还是能从C大调幻想曲或者《童年即景》(Kinderszenen) 中感受到罗伯特·舒曼的脆弱人生,从勃拉姆斯的晚期钢琴作品中思索其中表达的微妙而特殊的情感,从李斯特作品中重新欣赏他无边的幻想。
对里赫特的演出和录音的赞美之辞不胜枚举,但是所有赞美的共同点就是:无论里赫特是一往无前地突破技术可能性的极限,还是为了触键的诗意而自我克制,每个音符都体现出他是一位音乐家、一位艺术家、一种个性。
浏览 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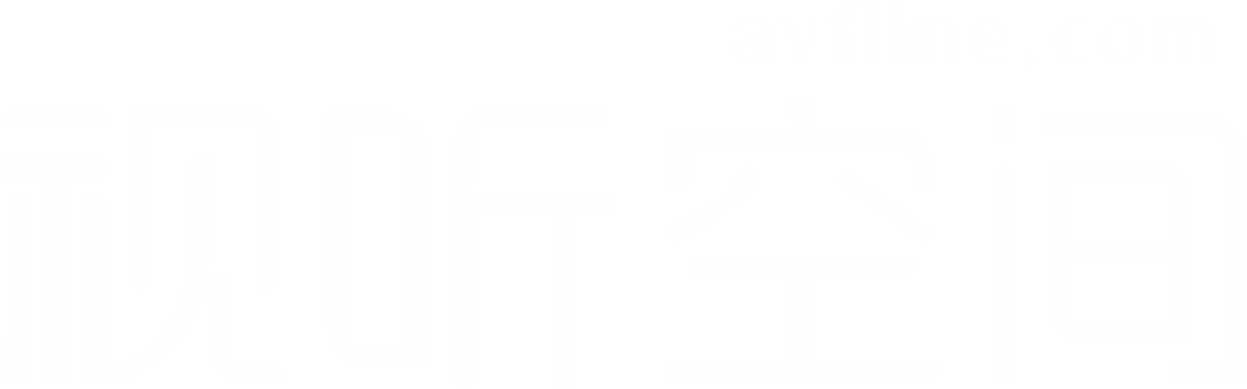








 新浪
新浪 淘宝
淘宝






